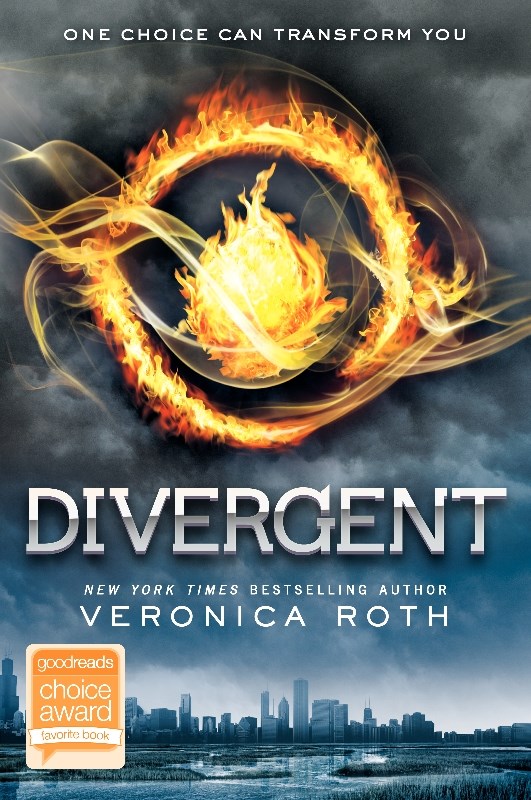
在未来的芝加哥,十六岁的比阿特丽斯·普莱斯必须在五个预定的派系中进行选择,以确定她一生中的身份,当她发现自己是一个不适合任何一个群体的异常时,这个决定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她所生活的社会毕竟并不完美。这是“Divergent”的摘录。
第一章
我家有一面镜子。它位于楼上走廊的滑动面板后面。我们的派系允许我在每三个月的第二天,即母亲剪头发的那一天站在它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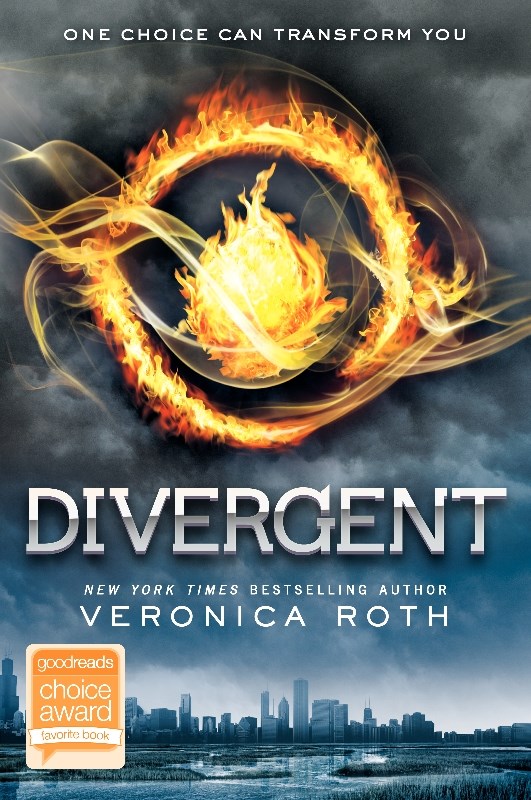
我坐在凳子上,母亲用剪刀站在我身后,修剪。这些绳子落在地板上,是一个沉闷的金色戒指.
当她完成时,她将我的头发从我的脸上拉开并将其扭曲成一个结。我注意到她看起来多么平静,她有多专注。她在失去自我的艺术中做得很好。我不能对自己说同样的话.
当她不注意时我偷看了我的反思 – 不是为了虚荣,而是出于好奇。一个人在三个月内出现很多事情。在我的反思中,我看到一张狭窄的脸,宽阔的圆眼,还有一个长而细的鼻子 – 我仍然看起来像个小女孩,虽然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变成了十六岁。其他派别庆祝生日,但我们没有。这将是自我放纵.
“那里,”当她把结打到位时,她说。她的眼睛在镜子里抓住我的眼睛。把目光移开是为时已晚,但不是骂我,而是对我们的反思微笑。我皱眉了一下。她为什么不谴责我盯着自己?
“所以今天就是这一天,”她说.
“是的,”我回答.
“你紧张吗?”
我盯着自己的眼睛看了一会儿。今天是能力测验的日子,它将向我展示我所属的五个派系中的哪一个。明天,在选举仪式上,我将决定派系;我将决定余生;我将决定留在家里或放弃他们.
“不,”我说。 “测试不必改变我们的选择。”
“对。”她笑了。 “我们去吃早餐吧。”
“谢谢。剪头发。“
她亲吻我的脸颊,将面板滑过镜子。我认为我的母亲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可能是美丽的。她的身体在灰色长袍下面很薄。她有高颧骨和长睫毛,当她晚上让她的头发下来时,它在她的肩膀上挂着波浪。但她必须在Abnegation中隐藏那美.
我们一起走到厨房。在这些早晨,当我哥哥吃早餐时,我父亲的手在读报纸的时候掠过我的头发,而我的母亲在她清理桌子的时候哼哼 – 这是在这些早晨,我觉得因为想离开他们而感到内疚.
公共汽车排气很臭。每当它撞到一块不平整的路面时,它就会让我从一边到另一边挤,即使我正在抓住座位以保持自己的静止.
我的哥哥迦勒站在过道上,头顶上方有栏杆以保持稳定。我们看起来不一样。他有我父亲的黑发和鼻子,以及我母亲的绿眼睛和酒窝脸颊。当他年轻的时候,那些特征看起来很奇怪,但现在它适合他。如果他不是Abnegation,我相信在学校的女孩会盯着他.
他还继承了我母亲的无私才能。他毫不犹豫地把他的座位交给了公共汽车上一位神勇的坎多人.
Candor男士穿着黑色西装,白色领带 – Candor标准制服。他们的派系重视诚实,将真相视为黑白,这就是他们所穿的.
当我们靠近市中心时,建筑物之间的缝隙狭窄,道路更加平滑。曾经被称为西尔斯大厦的建筑 – 我们称之为枢纽 – 从雾中出现,是天际线中的黑色柱子。巴士经过高架轨道。我从来没有去过火车,虽然他们从不停止跑步,到处都有铁轨。只有Dauntless骑他们.
五年前,Abnegation的志愿者建筑工人重新铺设了一些道路。他们从城市中心开始向外走,直到他们用尽了材料。我居住的道路仍然破裂而且不完整,驾驶它们并不安全。反正我们没有车.
当公共汽车在路上摇晃和颠簸时,迦勒的表情平静。灰色长袍从他的手臂上掉下来,因为他抓住一根杆子以保持平衡。我可以看出他眼睛的不断转变,他正在看着我们周围的人 – 努力只看到他们并忘记自己。 Candor重视诚实,但我们的派系,Abnegation,重视无私.
巴士停在学校门口,我站起来,掠过坦桑男子。当我偶然发现男人的鞋子时,我抓住Caleb的胳膊。我的休闲裤太长了,我从未如此优雅.
上层建筑是该市三所学校中最古老的建筑:低层,半山和高层。与周围的所有其他建筑一样,它由玻璃和钢制成。在它面前是一个大型的金属雕塑,Dauntless放学后爬,相互大胆越来越高。去年我看到其中一人跌倒并摔断了腿。我是那个跑去找护士的人.
“今天的能力测试,”我说。迦勒不比我大一岁,所以我们在同一年的学校.
当我们穿过前门时,他点点头。我们的肌肉收紧了我们走进来的第二个。气氛感觉很饿,就像每个十六岁的孩子在最后一天尽可能多地吞食一样。在选举仪式结束后我们很可能不会再走这些大厅 – 一旦我们选择,我们的新派系将负责完成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课程今天减少了一半,所以我们将在午餐后进行能力测试之前参加所有课程。我的心率已经升高了.
“你一点也不担心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我问迦勒.
我们停在走廊的分开处,他将走向一路,走向高级数学,我将走向另一个,走向派系历史.
他抬起头来看我。 “你是?”
我可以告诉他我几周来一直担心能力测试会告诉我什么 – Abnegation,Candor,Erudite,Amity或Dauntless?
相反,我微笑着说,“不是真的。”
他笑了笑。 “好 。 。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我走向Faction History,咀嚼着我的下嘴唇。他从不回答我的问题.
走廊狭窄,虽然透过窗户的光线营造出空间的幻觉;在我们这个年纪,他们是派系混合的唯一地方之一。今天人群有一种新的能量,最后一天狂热.
一个长卷发的女孩在我耳边喊着“嘿!”,向一位远方的朋友挥手致意。一件夹克套在我的脸颊上。然后一个身穿蓝色毛衣的博学男孩推我。我失去平衡,在地上摔倒.
“我的方式,僵硬,”他啪的一声,继续走下走廊.
我的脸颊温暖。我站起来把自己弄脏了。我摔倒时有几个人停了下来,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我。他们的眼睛跟着我走到走廊的边缘。现在,我的派系中的其他人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已经好几个月了 – 现在已经发布了有关Abnegation的反对报道,并且它已经开始影响我们在学校的关系。灰色的衣服,朴素的发型,以及我派系中不起眼的风度,应该让我更容易忘记自己,更容易让其他人忘记我。但现在他们让我成为目标.
我在E翼窗口停下来等待Dauntless到达。我每天早上都这样做。正好在7点25分,Dauntless通过从行驶中的火车上跳下来证明他们的勇敢.
我的父亲称无畏为“恶魔”。他们穿着,纹身,穿着黑色衣服。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我们城市周围的围栏。从什么,我不知道.
他们应该困扰我。我应该想知道什么是勇气 – 这是他们最有价值的美德 – 与你的鼻孔金属环有什么关系。相反,无论走到哪里,我的眼睛都会紧紧抓住它们.
火车哨声响起,声音在我的胸口响起。当火车冲过学校,在铁轨上发出尖叫声时,固定在火车前部的灯会发出咔嗒声。随着最后几辆汽车的通过,大量外出穿着深色衣服的年轻男女从投掷的汽车中摔倒,一些人跌落滚动,其他人则在重新获得平衡之前绊倒了几步。其中一个男孩搂着女孩的肩膀,笑着说.
看着它们是一种愚蠢的做法。我转身离开窗户,挤过人群进入派系历史教室.
第二章
测试在午餐后开始。我们坐在自助餐厅的长桌旁,测试管理员一次拨打十个名字,每个测试室一个。我坐在迦勒旁边,在我们的邻居苏珊对面.
苏珊的父亲为了他的工作而在整个城市旅行,所以他每天都有一辆车开着她上下学。他也提出要开车送我们,但正如Caleb所说,我们宁愿稍后离开也不想给他带来不便.
当然不是.
测试管理员大多是Abnegation志愿者,虽然其中一个测试室里有一个Erudite而另一个测试室里有一个Dauntless来测试我们这些来自Abnegation的人,因为规则规定我们不能由我们自己派系的人测试。规则还说我们不能以任何方式为测试做准备,所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的视线从苏珊漂到了整个房间的Dauntless桌子。他们笑着喊着打牌。在另一组表格中,Erudite在书籍和报纸上喋喋不休,不断追求知识.
一群黄色和红色的Amity女孩坐在自助餐厅的一个圆圈里,玩着一种涉及一首押韵歌曲的手拍游戏。每隔几分钟,我就会听到他们的笑声,因为有人被淘汰,必须坐在圆圈的中心。在他们旁边的桌子旁,Candor男孩用双手做出宽阔的姿势。他们似乎在争论什么,但一定不要认真,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微笑.
在Abnegation桌上,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派系习俗甚至决定了闲散行为并取代个人偏好。我怀疑所有的Erudite都想一直学习,或者每个Candor都喜欢热烈的辩论,但是他们不能无视我们的派系的规范。.
Caleb的名字在下一组中被调用。他自信地走向出口。我不需要祝他好运或向他保证他不应该紧张。他知道他属于哪里,据我所知,他一直都有。我对他的最早记忆来自于我们四岁的时候。他责骂我没有把我的跳绳送给操场上一个没有任何玩法的小女孩。他不再经常给我讲课,但我对他的表情不以为然.
我试图向他解释我的直觉与他的不同 – 它甚至没有进入我的脑海,让我的座位给公交车上的Candor男人 – 但他不明白。 “只要做你应该做的事,”他总是说。这对他来说很容易。它应该对我来说很容易.
我的胃扳手。我闭上眼睛,让它们关闭,直到十分钟后,迦勒再次坐下.
他脸色苍白。当我擦汗时,他像他一样用手掌推着他的手掌,当他把它们带回来时,他的手指在摇晃。我张开嘴问他什么,但话语没有来。我不被允许向他询问他的结果,他不允许告诉我.
Abnegation志愿者会说下一轮名字。两个来自Dauntless,两个来自Erudite,两个来自Amity,两个来自Candor,然后:“来自Abnegation:Susan Black和Beatrice Prior。”
我起床因为我应该,但如果由我决定,我将留在我的座位上剩下的时间。我觉得我的胸部有一个泡沫在第二个时间内膨胀得更多,有可能使我与内部分开。我跟着苏珊走了出口。我通过的人可能无法区分我们。我们穿同样的衣服,我们穿着同样的金发。唯一的区别是苏珊可能不会觉得她会呕吐,从我所知道的,她的双手并没有如此刻苦地摇晃她必须抓住她衬衫的下摆来稳住他们.
在自助餐厅外等候我们的是一排十间房。它们仅用于能力测试,因此我以前从未参与其中。与学校的其他房间不同,它们不是用玻璃隔开,而是用镜子隔开。我看着自己,脸色苍白,害怕,走向其中一扇门。她走进5号房间时,苏珊紧张地笑着对我说,我走进6号房间,一个大无畏的女人在等我.
她没有像我见过的年轻无畏者一样严肃。她有着小而黑的棱角分明的眼睛,穿着黑色西装外套,就像男士西装和牛仔裤。只有当她转身关上门时,我看到她脖子后面有一个纹身,一只黑眼睛的红眼鹰。如果我不觉得我的心脏已经迁移到我的喉咙,我会问她这意味着什么。它必须表示某种意义.
镜子覆盖了房间的内壁。我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到我的反射:灰色的织物遮住了我背部的形状,我的长脖子,我的结节指针,红色的血腮。天花板发光白光。在房间的中央是一个斜倚的椅子,像牙医一样,旁边有一台机器。它看起来像一个发生可怕事情的地方.
“别担心,”这位女士说,“它没有受伤。”
她的头发是黑色和笔直的,但在光线下,我看到它的头发是灰色的.
她说:“坐下来舒服一点。” “我叫Tori。”
我笨拙地坐在椅子上,斜靠在头枕上。灯光伤害了我的眼睛。 Tori在我右边的机器上忙忙碌碌。我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而不是她手上的电线上.
“为什么是鹰?”我脱口而出,因为她在前额上贴了一个电极.
“从来没有遇到过好奇的憎恶,”她说,抬起眉毛看着我.
我颤抖着,手臂上出现了鸡皮疙瘩。我的好奇心是一种错误,是对Abnegation价值观的背叛.
哼了一声,她将另一个电极压在我的额头上,并解释说:“在古代世界的某些地方,鹰象征着太阳。回到我得到这个的时候,我想如果我总是把太阳照在我身上,我就不会害怕黑暗。“
我试图阻止自己提出另一个问题,但我无法帮助它。 “你害怕黑暗?”
“我害怕黑暗,”她纠正我。她将下一个电极按到她自己的额头上,然后将电线连接到它上面。她耸了耸肩。 “现在它让我想起了我已经克服的恐惧。”
她站在我身后。我把扶手挤得那么紧,红色从我的指关节拉开。她将电线拉向她,将它们连接到我身上,连接到她身上,连接到她身后的机器上。然后她递给我一瓶清澈的液体.
“喝这个,”她说.
“这是什么?”我的喉咙感到肿胀。我努力吞咽。 “会发生什么事?”
“不能告诉你。相信我。”
我从肺部按压空气,将小瓶中的内容物倒入口中。我的眼睛闭上了.
当他们打开时,瞬间过去了,但我在其他地方。我再次站在学校的自助餐厅,但所有的长桌都是空的,我透过玻璃墙看到它在下雪。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有两个篮子。其中一个是一大块奶酪,另一个是前臂长度的刀.
在我身后,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选择。”
“为什么?”我问道.
“选择,”她重复道.
我看着我的肩膀,但没有人在那里。我转回篮子。 “我会怎么处理他们?”
“选择!”她喊道.
当她对我尖叫时,我的恐惧消失了,顽固的取代了它。我皱眉,交叉双臂.
“按你自己的方式行事,”她说.
篮子消失了。我听到门吱吱嘎嘎地转过身来看看它是谁。我看不到“谁”而是“什么”:尖鼻子的狗站在离我几码远的地方。它蹲伏在我的身上,它的嘴唇从白色的牙齿上脱落。咆哮声从喉咙深处咕噜咕噜地响起,我明白为什么奶酪会派上用场。还是刀。但现在已经太晚了.
我想跑步,但狗会比我快。我不能把它摔到地上。我头疼。我必须做出决定。如果我可以跳过其中一张桌子并将其作为盾牌使用,那么我太矮了,无法跳过桌子,而且还不够坚固,无法将其翻过来.
狗咆哮着,我几乎感觉到声音在我的头骨中振动.
我的生物学教科书说,狗可以闻到恐惧,因为人体腺体在胁迫状态下分泌的化学物质,与狗的猎物分泌的化学物质相同。嗅到恐惧会导致他们受到攻击。狗朝我走来,它的指甲刮到了地板上.
我跑不了。我不能打架。相反,我呼吸着狗的臭气味,尽量不要考虑它刚吃的东西。它的眼睛里没有白色,只有黑色的光芒.
我对狗还有什么了解?我不应该看它的眼睛。这是侵略的迹象。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问我的父亲是一只宠物狗,现在,盯着狗爪子前面的地面,我记不起为什么了。它越来越近,仍在咆哮。如果凝视它的眼睛是侵略的标志,那是什么表示屈服?
我的呼吸很响,但很稳定。我跪倒在地。我想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躺在狗的前面,让我的牙齿与我的脸平齐 – 但这是我最好的选择。我伸出双腿,靠在肘部。狗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我感到脸上的温暖气息。我的手臂在颤抖.
它在我耳边吠叫,我咬紧牙关以防止尖叫.
粗糙和潮湿的东西触动了我的脸颊。狗的咆哮停止了,当我抬起头再看一遍时,它气喘吁吁。它舔了舔我的脸。我皱眉,坐在我的脚跟上。那条狗把它的爪子撑到我的膝盖上,舔着我的下巴。我畏缩,擦掉皮肤上的口水,然后大笑.
“你不是一个恶毒的野兽,对吧?”
我慢慢起来所以我不会惊慌失措,但它似乎与几秒钟前面对我的动物不同。我小心地伸出一只手,如果需要,我可以把它拉回来。狗用头轻轻推开我的手。我突然很高兴我没拿起刀.
我眨了眨眼,当我的眼睛睁开时,一个小孩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站在房间对面。她伸出双手和尖叫声,“小狗!”
当她跑向我身边的狗时,我张开嘴向她发出警告,但我来不及了。狗转身。它不是咆哮,而是吠叫,咆哮和拍打,它的肌肉像卷线一样堆起来。即将突袭。我不认为,我只是跳;我将我的身体扔在狗的上方,将我的手臂环绕在厚厚的脖子上.
我的头撞到了地上。狗走了,小女孩也走了。相反,我一个人 – 在测试室,现在是空的。我转过一个慢圈,看不到自己在任何一面镜子里。我把门推开,走进走廊,但它不是走廊;这是一辆公共汽车,所有的座位都被占用了.
我站在过道上,坚持一根杆子。坐在我附近的是一个有报纸的男人。我看不到他的脸在纸的顶部,但我可以看到他的手。他们伤痕累累,就像他被烧了一样,他们围着纸张紧握,就像他想要弄皱一样.
“你认识这个人吗?”他问道。他在报纸的头版点击了这张照片。标题写着:“野蛮凶手终于被逮捕了!”我盯着“杀人犯”这个词。自从我上次读到这个词以来已经很久了,但即便是它的形状也让我感到害怕.
标题下面的照片是一个平凡的脸和胡须的年轻人。我觉得我确实认识他,虽然我不记得怎么样。与此同时,我觉得告诉那个男人是个坏主意.
“好吧?”我的声音听到了愤怒。 “你做?”
一个坏主意 – 不,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我的心脏挣扎,我抓住杆子以防止我的手颤抖,不让我离开。如果我告诉他我从文章中认识那个男人,那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我可以说服他,我没有。我可以清理我的喉咙并耸肩 – 但那将是一个谎言.
我清了清嗓子.
“你呢?”他重复道.
我耸了耸肩.
“好?”
一阵颤栗穿过我。我的恐惧是不合理的;这只是一个测试,它不是真实的。 “不,”我说,我的声音随意。 “不知道他是谁。”
他站起来,最后我看到了他的脸。他戴着深色太阳镜,嘴巴弯成一团。他的脸颊上有疤痕,就像他的双手一样。他靠近我的脸。他的口气闻起来像香烟。不是真的,我提醒自己。不是真的.
“你撒谎,”他说。 “你在撒谎!”
“我不是。”
“我能在你眼中看到它。”
我把自己拉得更直。 “你做不到。”
“如果你认识他,”他低声说道,“你可以救我。你救了我!“
我眯起眼睛。 “好吧,”我说。我下巴了。 “我不。”
摘自Veronica Roth的“Divergent”。版权所有©2011 Veronica Roth。经HarperCollinsPublishers印记Katherine Tegen Books许可转载. 版权所有。印在美利坚合众国. 未经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或复制本书的任何部分,除非在批评性文章和评论中体现了简短的引用。有关信息,请参阅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HarperCollins Publishers的一个部门,纽约东53街,纽约,纽约10022.
